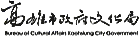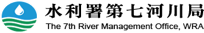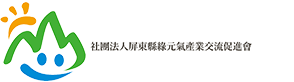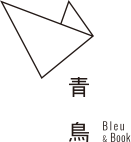1972年,蔣勳25歲,滿懷著對歐洲偉大文明、優雅傳統的憧憬,意氣風發地來到巴黎大學攻讀藝術,完全沒想到真正的法國、乃至於全世界,竟是這般場景。
當時雖然離1968年的五月風暴已過去四年,但巴黎還餘波盪漾:高達(Jean-Luc Godard)為1968學運街頭拍攝的電影《一切安好》(Tout va bien)是年上映,電影裡滿是當時群眾激亢的陳詞 ,校園裡的美麗雕像上仍滿是紅色噴漆,他還記得上課上到一半,樓下碰的一聲爆炸,就有屍體被抬出去了;隔年,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被暗殺⋯⋯種種原先所羨慕的、憧憬的全都是資本主義、都要被批判打碎。「我簡直嚇得快昏倒,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蔣勳回憶。
時而開始,時而結束;時而激情奮起,時而面對恐怖
那是一個全世界政局動盪、文藝青年燃燒熱情的年代。「1973年王禎和完成美國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訪問作家行程,經過巴黎住我那裡,他說那時他雖然在美國,但每天都在看樣板戲,每個人都被打動了,」蔣勳轉述王禎和的記憶說,當時每個人都想著不要自己的名利、如何把自己奉獻出去?
1970年代中期,蔣勳去美國柏克萊訪問,台灣作家陳若曦帶著他逛校園,指著校內的鐘樓說,在學運最狂熱的時候,那個鐘樓一天早中晚三次放〈東方紅〉。
**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咳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主席,愛人民,他是我們的帶路人。為了建設新中國,呼兒咳呀,領導我們向前進。
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哪裡有了共產黨,呼兒咳呀,哪裡人民得解放。
**
因著歌中勾勒的理想,1966年,在台灣土生土長的陳若曦與丈夫段世堯懷抱著對社會主義及毛澤東思想的憧憬,放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學位,去到中國,那一年也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她跟著下鄉去修淮河,扛土、修堤防,也因此腰部受了很嚴重的傷。
外界風起雲湧,台灣內部卻因為兩蔣厲行戒嚴,肅清左翼,是極端反動。1968年4月,文星書店被勒令停業;7月,台灣當局以「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逮捕陳映真,由於陳映真為《文學季刊》的編輯委員,季刊相關文人黃春明、尉天驄、王禎和也遭到牽連;1971年,李敖也被捕下獄。
蔣勳細數著,台灣的68世代還要算上郭松棻。郭松棻的父親是台灣士紳、膠彩畫大師郭雪湖,書又讀得極好,進入聯合國擔任翻譯,後來他全力投入保衛釣魚台運動,甚至為此放棄了博士學位,只因思想左傾,就被列入國民黨政府黑名單,長期不准回台灣。
「他們現在都不願意講68,因為事實上,後來都幻滅了。」蔣勳感嘆,陳若曦1973年離開中國,在美國將中國的見聞寫成諷刺的寫實小說《尹縣長》。郭松棻的理想也幻滅了,「他過世前都不太願意跟人往來,但我相信如果沒有1968的燃燒和幻滅,不會出現郭松棻很精采的文學小說,像是《雙月記》裡的〈月印〉,」蔣勳感嘆。
「他們不講,我哪有資格談1968?我手上乾乾淨淨的,」蔣勳苦笑著說,但那真是個瘋狂又荒謬的年代,他們都被燃燒了,那些心情好動人,經歷其中的人應該會覺得很過癮,但由於政治、由於歷史演變、由於各種顧慮⋯⋯更由於事到如今。
「有時候我會想,在鄉下隱居的陳若曦,會不會扶著腰,想著自己這一生有沒有白活?」蔣勳悠遠地想著。
革自己的命,可以放棄階級性到什麼程度?
「在那之中,你慢慢會發現,他們真正要革命的對象不是強人戴高樂、不是資本主義,而是自己,對自己革命,」蔣勳說,這些68的領袖其實都有很好的社經條件、只要穩穩地拿到博士、就可繼續往社會上層走,但他們都沒有。
以導演高達來說,他出身富裕,父親是醫生、母親是瑞士銀行家之女,但他認為好萊塢電影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所以整個學運他就拿著手搖錄影機,拍下所有的街頭運動。當時他的革命伴侶Anne-Marie Miéville出身也相當顯赫,但為了高達改造自己。
又或是法國現在有名的文學期刊《Tel Quel》(譯:《如是》雜誌)創辦人Philippe Sollers和他太太Julia Kristeva,總穿著一身毛裝(毛澤東服),常往中國跑,甚至用文革的觀點批判法國當局。「他們很有爭議,但我覺得這也沒有不好,畢竟時代不能完全不被懷疑,不過也因為我跟他們熟,就會發現他們就算穿毛裝,剪裁也跟別人不一樣,即便他們在講革命,但松露還是不能少的,因為他們都是從最好的家庭出來的,最想革自己的命,但沒辦法完全徹底。」蔣勳說,外人很難看出來,總覺得他們講話行為很教條,跟他們當朋友後就會發現,他們的人生有很多衝突和複雜,但他們想去挑戰自我階級性,可以放棄到什麼程度。
陳若曦、郭松棻、劉大任等也都是,他們明明都已經在國外最好的大學、快拿到博士學位了,卻還是砰地丟下一切,就去追尋理想、去睡在淮河邊上、去保衛釣魚台,這對藝術家創作是很好的,即便有很多矛盾——事實上正因為有這些矛盾,才會有他們了不起的創作。
所以蔣勳認為,台灣應該好好地整理這些故事,該讓20歲的人聽聽看,讓他們想想自己的20歲能做些什麼,30歲就太晚了。
如何整理台灣的68定位?將是當代共同課題
事實上,68思潮對台灣文化界造成相當大的影響,蔣勳稱之為「廣義的」鄉土運動濫觴。「在那之前,亞洲都還是西方的殖民地,但1968之後,大家開始省思,亞洲雖然是弱勢,但能不能有自我?能不能找到自信?」
對蔣勳來說,68精神就是下鄉奉獻,且從那之後,這股思潮延燒到各個領域。
音樂界的代表就是史惟亮和許常惠。他們從歐洲返台後,沒有在台北發揮所謂「偉大的西方音樂主流」,而是下鄉收集台灣在地的民謠與音樂文化,所以才在恆春找到陳達、在滿州鄉找到曾徐茂妹。
藝術界亦受到影響,1972年林懷民返國,開始嘗試把舞蹈家瑪莎.葛蘭姆技巧轉向表達中國元素,所以1973年成立雲門舞集,1975年《白蛇傳》首演,找來賴德和作曲、楊英風做舞台佈置。
70到80年代台灣小劇場非常蓬勃,街頭運動全都是小劇場的人主導,蔣勳說,當時有好幾個極具代表性的劇場如蘭陵、田啟元的〈白水〉,「那是台灣很棒的時代,年輕人會把他所學的建築、劇場、藝術跟時事批判做結合,現在反而比較少。」
攝影界的改變最直接。在此之前,台灣攝影是中國攝影學會主導,不是氣勢恢弘的山水、就是美女擺拍,但張照堂這批人走向報導、去拍很多民間的東西,跟主流的沙龍有所區隔,主題可以是樂生療養院、東部傳教士群像或是工運工殤等。
建築界則有夏鑄九於1976回國,在台大創建了城鄉所,帶著學生參與街頭運動,與無殼蝸牛抗爭,本來台灣建築也沒有這一塊。現在持續有繼承68精神的,應該算是謝英俊,921之後他就在高屏地區投入災後重建的工作,直到現在。
今年蔣勳去巴黎避暑,期間看了法國電視台所做的1968專題,當中遍訪了全世界68世代參與者,談事發經過以及事件對他們的影響,國家檔案局也公布所有68年的國家檔案,進行大型展覽。
他觀察到,年輕人也去看這些展覽,雖然跟他們很遙遠,但絕大數的人還是肯定1968。「我覺得大家肯定的不是1968那年發生所有事件,而是一個精神狀態,每一個20幾歲的人都應該要有1968的夢想,那是跟權威、社會既得利益者劃清界線,保有自己的單純性,就是68的核心價值。」
**
〈美麗島〉
詞/梁景峰 曲/李雙澤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們正視著,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複的叮嚀,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複的叮嚀,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
**
台灣的68世代和後68思潮躍進如此精彩,可惜的是,他們自己不談,台灣人又健忘,整理歷史的能力特別弱,再加上受到政治立場的干擾,太快下結論,就看不到世代的延續性。〈美麗島〉這首民歌,及其作者李雙澤——在當時有台灣Bob Dylon之稱的畫家、作曲家,就是一個非常值得反思的例子。
蔣勳說,絕大多數的人以為它是民進黨的黨歌,蔡英文選它在就職典禮上合唱,但很多人並不知道有一陣子它曾是救國團團歌,大家都在學,後來發現跟台獨有關,才被國民黨政府被禁掉,但黨外人士又把它拿來當成理想,辦了〈美麗島〉雜誌等,一下子被認同,一下子不被認同。所以一次林懷民突發奇想地問,「要是李雙澤現在還活著,該是統派還是台獨?」他一時為之語塞,「所以他死得早也好,不用面對後面那些問題,」蔣勳半開玩笑地說,但話中帶著苦澀。
蔣勳說,當時他和林懷民、李雙澤、胡德夫都是文化圈好友,李雙澤1977年為了救人自己卻溺斃,告別式那天,大家一起唱〈美麗島〉送他,李雙澤最好的哥兒們——視障歌手莫那能卻在大家唱完後說,「我每次聽到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這句,就想到你們漢人一啟山林,就是我們原住民族流離失所。」蔣勳坦言,他們聽到時真的怔住了,作為一個漢族移民,永遠不知道原住民族怎麼看你,「我們應該要聽到這個聲音,但不是要急著下結論,而是要先反省,台灣史才會比較有寬闊、恢弘的可能性。他認為,這將對整個台灣來說,都將是一個很棒的題目。
(文/洪辰芳、攝/林煜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