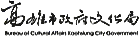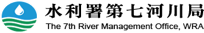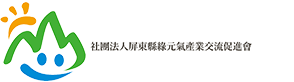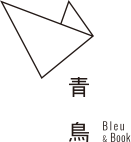「我早就想參加朗讀節了!」以講述美學文學享譽華人世界的藝術家暨作家蔣勳,今年終於趕上參與華文朗讀節,並將於10月 4日開幕場上,從「不遙遠的歌聲:漢語詩的格律與朗讀」為題發表演說。
漢詩?很有距離吧;格律?略顯陳腐?但蔣勳講的可是掀起一場「聽覺革命」。他觀察到,現代人太倚賴視覺,反而讓聽覺跟視覺產生了錯離、漢語和漢字互為侷限,台灣民間有很多極具生命力的聲音,應該要把他們找回來。蔣勳也為此特別用心鋪排了本次開幕節目,朗讀節團隊特別請他於百忙之中先為朗讀節聽眾「劇透」部分講題內容,以下為專訪輯要:
華文朗讀節團隊問(以下簡稱Q):這是您第一次參加朗讀節,可否說說為什麼今年有這個機緣?
蔣勳答(以下簡稱A):對,其實我一直很想參加,可是每一年的時間我剛好都在國外,我夏天通常不在台灣,今年時間正好趕上,所以主辦單位開口邀約,我就一口答應。
我覺得朗讀非常、非常重要,現代人視覺用得太多、聽覺用得太少。很多孩子看電影或看電視,明明講的是他聽得懂的華語,可是一定看字幕,如果沒有字幕,聽覺就會變得非常不準確,連我自己後來都提醒自己不要太倚賴字幕。
這背後凸顯一個問題:現在播報員或演員的發音是有問題的。所謂「咬文嚼字」,字是要用「咬出來的」,一個一個清清楚楚,但現在連歌也不容易聽懂。就像周杰倫唱什麼我根本就聽不懂,他們說他好就好在聽不懂。可是以前不是啊,京劇演員顧正秋一唱,每一個字都會打到你心裡去,所以聽覺跟視覺產生了一種錯離的現象。
其實台灣民間很早就有朗讀,1967年音樂家史惟亮與許常惠進行戰後台灣最大規模的「民樂」採集,在恆春發現了陳達,他不識字、沒有受過教育,完全靠聽覺記憶,但月琴一刷,他開口彈唱「思啊想啊起~」,你就會被他震懾住。
我記得很清楚,1978年,林懷民請他為舞作《薪傳》錄製配樂,那天把我嚇壞了,因為他在錄音室裡,完全是即興的吟唱,但每一句都是七個字還都押韻,聲音準確性之高,一唱五個小時都沒停(編按:後來《薪傳》只取其中一部分作為演出的「間奏曲」)。
但我真正意識到我們的語言能力喪失得非常嚴重,是看到我們的政治領導,每一個人都在唸稿,反觀美國總統歐巴馬的卸任演說,那語言真是漂亮,連中國大陸的年輕人的語言,也比台灣人厲害,他們很敢發言,而且條理分明,這是台灣應重視的問題。
言說比文字的表達更直接、感受更深刻
Q:您的演說就非常受到歡迎,總能信手捻來卻是引經據典,這背後做了很多苦功?
A:我要感謝我的時代,我最早的感官經驗是用聽的,不是看的。
入學前我母親就會常常念唐詩、宋詞、戲曲給我聽,甚至會唱一段。我在台北大龍峒長大,一年大概有三個月廟口都在演歌仔戲,小時候也在那邊聽,都沒有字幕。小時候最喜歡看布袋戲,小朋友全部逃學,趴在那邊看,後來才知道那就是國寶級布袋戲操偶師李天祿,布袋戲偶一出場,李天祿念那出場詩之漂亮,這個口述系統一直到黃俊雄其實都還有,節奏鏗鏘,聽覺上極有魅力。
在我那個年代,在廟口要賣藥也必須要有一套,因為有台語、客語、來自大江南北各路人馬,要吸引人家停下來,不管〈蓮花落〉還是什麼東西都要立刻唱出來。清朝以前識字的人僅佔總人口2%,所以民間最早教育是靠傳唱、朗讀傳的,有非常強的傳唱文學,像南管、北管、蘇州評彈等,對大眾的影響力是大過文字。
我一直在想要怎麼喚起大家對聽覺的重視,現在有一個切入點,是書店沒落了,換句話說,就是文字沒落了,新的教育方式讓孩子們開始能從圖像跟聲音裡找到新的感覺,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你也會發現,現在有聲書影響力愈來愈大,我在中國最大的音頻網站蜻蜓FM上的《細說紅樓夢》,下載人次超過2.3億人。
聽覺其實也是比視覺更親密的行為,我跟媽媽很親,是因為她一直在我耳邊講故事,她的聲音對我來說就是一種記憶。聽覺跟心跳、呼吸的關係比較密切,音樂也比較容易讓人感動到想哭,畫作感染力就沒有那麼強。
可是又有一點我又很怕朗讀,中學的時候,文青都會被弄去詩社朗誦,但那一陣子台灣的學校文青的朗誦詩變得很肉麻的,聽了會讓人雞皮疙瘩起來。我覺得只要是用最真摯的心情朗誦,應該就很動人,我聽過很好的,像是余光中的朗讀、瘂弦的朗讀、周夢蝶的朗讀,管管的有一點表演,但也都有他的特色,因為是跟個性是在一起的,向陽的台語朗讀也漂亮的不得了,所以其實台灣應該有很好的當代朗讀典範,但也不知道為什麼詩社一直沒有改。我曾當過政大長廊詩社評審,唉⋯⋯但又不好意思講,因為文青總是可愛的啊,可是你聽了以後還是會覺得,哎唷怎麼會把許悔之的詩念成這樣?詩一定有一個很真誠的意涵,但他們的念法反而變得很刻意的造作,我覺得那個很危險。
音韻格律能讓文字更具感染力
Q:您看兩岸華文界,中國流行朗讀嗎?他聽,可是他們朗讀嗎?
A:也不太,他們有他們自己傳統,我在上海聽過評彈,他們的語言能力真的很強,但我不喜歡很「表演」的東西。詩的朗讀不能完全表演,因為完全表演後,會偏離那個很動心的部分,應該讓朗讀變成一種訴說心聲,如泣如訴;他甚至不一定是字句,而是一個聲音的感覺,所以我覺得朗讀真的很難。
西方本身是拼音文字,所以書寫是和聲音一起的,漢語是視覺(象形)文字,會受到文字的視覺干擾,所以在把視覺轉成聽覺時是有難度。我很喜歡聽不同地區他們怎麼去表達聲音,不一定是朗讀,比如在貴州、安順有茶山情歌,是即興的,台灣也有,現在在桃園的文昌公園每個禮拜天早上還有「公園仔相褒」,那些退休的工人、採茶工,你一言我一句對唱,這些都是台灣民間很強的生命力,我很希望能夠再恢復這些聲音。即便是今天年輕人拿個吉他隨便彈唱,或者講一段、唱一段,就是朗讀,但現在台灣大眾有一種沈默,讓你覺得好⋯⋯好奇怪喔,大家都沒有聲音。
Q:也許是您很早之前的《孤獨六講》裡的那六種孤獨又充斥了整個社會?
A:《孤獨六講》其實也是用講的,後來才用文字紀錄下來,所以我一直相信「講」真的可以整理出東西,就是你自己相信你的語言。
你下次注意一下,你跟一個朋友在交談中,讀懂了他的心情,然後你試圖用聲音(而不是用文字)跟他交換心事,一定可以測到他表情上慢慢、慢慢地變化。我做老師,學生來找你的時候,你會發現他等待的不一定是你給他人生上什麼格言指引,其實是聲音,聲音本身有安慰的力量。
西藏喇嘛的誦經是非常動人的,會讓你起雞皮疙瘩,忽然一下子汗毛都立起來了。他們有各種的咒,我曾聽過一種咒,完全不知道意思,但不自覺地就趕快端坐起來,那力量強到能透過空氣的頻率震撼你。我後來才知道那是一個很重的咒,發願把腦挖出來去供養惡鬼。所以我一直覺得聲音是有很高很高的傳達性。
歐洲基督教經文唱詩也有相同的力量。現在很多福音唱詩不是在錄音間錄,而是在教堂錄,因為他們發現在教堂裡的共鳴跟錄音間是不一樣的,會會達到一個更強大的感染力。
這些都是聲音的資料,我希望讓大眾更珍惜聲音的資料,慢慢整理出來,讓人們可以用聲音來溝通心事。但是我們的聲音教育很差,最難聽的聲音就是在立法院,叫囂是很不好的示範,為什麼不能用一個比較溫和的聲音來溝通、說服或感動,而要這麼嘶吼?一到選舉,更讓我想快點跑掉,而那種聲音對民眾感染很大,連在捷運裡也指著人說:欸你為什麼坐我的博愛座?
Q:現在人可能太執著在視覺上的絢麗,其實不是很在乎聲音的變化?
A:對,古希臘有修辭學、辯論術,要在廣場上大聲演說,講到能說服他人,就是重視聲音這個要素,每一個人要發表意見的時候他要在那個扇形空間,我們沒有這個傳統,也難怪我們的政治領導的語言能力真的好差、好差⋯⋯
《詩經》是從聽覺出發的,莊子、孔子這些人也是「講學」,後來才被記錄下來,大部分並不是文字書寫,所以他們當年一定有很好的語言的能力。佛經則更驚人,全部是用講的,「如是我聞⋯⋯」當時有人在現場紀錄,那這些人都是靠語言言說,沒有言說沒有這麼動人的經典,不管是華人的經典、印度的經典、荷馬史詩的傳唱。
但人類進入到文字階段以後,文字就變成一種視覺符號,語言反而沒落下去,可是現在可能藉著3C產品這樣的情況,語言應該要再起來一次。
Q:所以您這次在朗讀節開幕上的分享,會從詩詞的格律來談?
A:語言能感動人心一定要有格律。詩人聞一多稱之為「音尺」,聲音的尺寸。他說,雖然在胡適白話文運動後,現代詩/白話詩不再講格律,但只要是詩一定要有音尺。所以我有段時間我很喜歡朗讀聞一多的詩,能感覺到他的起伏跌宕、平仄音韻、子音跟母音的關係,其實就是他對聲音本身的了解。
後來我相信古代的詩人大概都是一個好的歌手——廣義的歌手——他對聲音是非常的理解。我們現在已經流失了,不知道怎麼唱詞,但如果你大聲地唸蘇東坡,大聲的唸柳永,你會覺得真的不一樣,蘇東坡就須關西大漢,以銅琵琶、鐵綽板彈唱「大江東去!」而柳永就要是十七八歲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因為節奏一個輕一個重,一個像貝多芬、一個像莫札特,真的不一樣。
Q:不過很多流行歌手嘗試做一些台語歌,但詞與曲上好像總是一點不對味?
A:可是江蕙很好啊,真的很棒啊。主要是她表達的聲音,一句「酒若入喉⋯⋯」噢,就真的讓你覺得整個肺腑在震動,那真的是好啊。所以我覺得大眾其實懂欸,她真的是打中台灣好多底層人的心情。
胡德夫聲音也好啊,很可惜他大部分是用漢語在唱,如果用他原住民的語言唱,我相信更漂亮。還好我們現在有桑布伊,你完全聽不懂他內容,可是聲音真是漂亮。
我是在紐約中央公園散步時,聽到桑布伊的聲音。一聽到這個聲音啊,我立刻知道是桑布伊,就去找他,那天是紐約市舉辦的台灣日,在那個聲音之外圍滿了來自世界各國的人,都被那個聲音震動。
我後來也找桑布伊一起來製作雲門的舞作《關於島嶼》,當中我是朗讀多位台灣詩人的詩,可是桑布伊聲音一出來我就嚇壞了,他的部落是沒有文字的,卻也因為沒有文字,所以語言是強度可以這麼高,我們太自豪於文字,結果聲音在沒落。
所以我覺得台灣是有很好、很好的聲音,至於漢字跟漢語之間,怎麼樣找到一個新的關係,真的很適合以朗讀節為平台繼續挖掘下去,會很有趣,然後找更年輕的一代來參加,一定會愈來愈精采。
(文/柯鈞彧、攝/林煜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