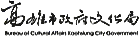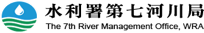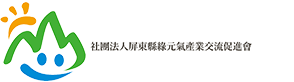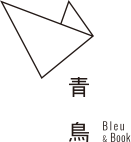想像一下每天的日常:出門、搭捷運、進公司、打電腦,用餐之後再打電腦,然後搭捷運回家。原本也該如此的今日,突然從捷運站走到公司的路上,撞見一隻母雞。你停下來開始思考,雞是從哪裡來?又要到哪裡去?現在我該做些什麼?
這就是生活戲劇化的瞬間:當發生一件不在預期內的事件,中斷了原本的模式,進而觸發人們的想像。而這也是劇場導演楊景翔與陳仕瑛希望能在華文朗讀節中創造的體驗。
對兩位來說,過去都曾有處理以詩為文本的演出經驗,然而這次合作最大的不同,楊景翔認為,「相對處理劇場文本,我們是在服務文本或發掘文本,比方雕塑角色、場景、情境,但這一次是以人為主,發掘作者的可能性。」為了找到作者的可能,導演與20檔節目的講者碰面溝通,了解當下的想法。而這個「當下性」即具備了「劇場」的內涵。
除了理解作者想法,協助轉化呈現外,導演們也試著嘗試不同的可能。比方讀劇〈春眠〉便將講座與讀劇結合,形成最近台灣開始討論的「講座式展演(Lecture Performance)」。節目企劃一開始找來影視、劇場編劇來讀劇,與傳統找演員來詮釋便是不一樣的角度。楊景翔認為編劇特別之處在於對劇本的理解與想法,是整體的概念;而演員是從詮釋角色的角度去分析劇本。加上音樂人及脫口秀演員日京江羽人的加入,發展成講座與表演交錯的模式:當讀劇讀到一個段落,會停下來進行討論,再繼續讀劇。這將是個不斷中斷的演出,也許與傳統讀劇相比少了些表演性,但多了更多互動與思考。
劇場即生活
結合講座與劇場的模式,國外早已行之有年。因此對楊景翔來說,形式一直都存在,只是是否流行而已。而陳仕瑛認為,劇場介入任何形式都是好的。「大家對劇場這個表演藝術有些偏見,覺得它門檻很高,一般人可能也會認為,會不會看不懂?但事實上劇場元素在我們的生活裡,無所不在。」
回應陳仕瑛的看法,楊景翔補充,像是一戰時期發展的前衛藝術、達達主義,人們會在酒館裡頭唸詩。甚至他小時候看野台戲,也算是劇場的一種。「現在很多人講『劇場』還是在講『舞台劇』,是鏡框式舞台,坐在國家戲劇院,軟軟的、絨布椅子上,才叫進劇場,其實並不是,一開始並不是這樣。」
陳仕瑛提到,「這次的活動空間反而提供了自由度和彈性,比方說常來青鳥書店的人,在活動期間可能會發現,原來這個空間可以處於非書店的狀態,對一般不常接觸表演藝術的觀眾來講,那是一個蠻大的驚喜。就像我們在西門町,走出捷運站時看到一些表演,你停下來看了一下,就會覺得今天好像有點不一樣。」
朗讀,共享彼此的當下
「朗讀」或「讀劇」對劇場導演來說不算新鮮事,那麼兩位過去曾有印象深刻的朗讀經驗嗎?楊景翔說,在他國中的時候,國文老師找來了鄉下的阿公,用台語唸蘇東坡的詩。在過去唸這些詩的時候,從不曾真正感覺到裡頭的音律、抑揚頓挫,卻在那個課堂感受到了。「以一個台語人來說,中文對我來說是第二語言,有些東西都要轉個彎去想。那反而是讓我感受到切身連結的經驗。」
陳仕瑛回想,一次和朋友一起爬山,在半山腰小憩時,朋友拿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閱讀。當時她向朋友提議要不要把書的內容朗讀出來?於是陳仕瑛有了在山嵐間聆聽朗讀的經驗。「就像電影《為愛朗讀》,朗讀變成一種很特別的溝通方式,我現在在看的東西、我現在讀出來給你聽,彼此共享了這個狀態。」
聊了劇場、談了朗讀,總歸來說這次導演所扮演的角色,楊景翔以過去曾看過的展演經驗作結:前年的愛丁堡藝穗節,他在電影院看了一檔節目《History History History》。加拿大藝術家 Deborah Pearson 放映一部 1956 年由他外公主演的匈牙利電影,播放的當下他一邊上字幕,透過這部電影講述他的家族故事。雖然沒有像想像中典型的表演,但看完仍令楊景翔十分感動。「劇場有時候也沒有表演,就只是把一些有故事的元素、有重量的故事放進去。就像我們這次整體的展演一樣,他們都是作者,不一定要表演,他們有大量的知識及表達能力,而我們就是找一個適合他們的方式,把他們放進去。如此而已。」就像詩人洛夫曾說,「所謂詩,就是把最適當的字擺在最適當的位置。」
(文/史比野塔;攝/李沛岑)